月陇西有心思美酒佳肴,她却连筷子都没动一下,满脑都是案子。<br>霍齐说,沈庭曾玷污过他的妻子,后来他的妻子想不开撇下他和孩子投河自尽,他去找沈庭讨要说法,沈府拒不承认,还将他打得人事不省,扔进山里,若不是他命大,险些就喂了山中野狼。等他再摸回家时,孩子也不知去向。<br>因此,他与沈庭之仇不共戴天。这件事几乎没有别的人知道,山民都只道他是外地来的,也不问他的过去。<br>他谋划许久,终于想到这么个方法,势必要把沈庭置于死地。<br>他知道沈庭常去照渠楼休憩,傍晚他就潜入后房,在沈庭常住的房间塞了纸条,而后迅速离去,等在茶坊。<br>沈庭果然赴约,他迷晕沈庭之后就将他绑了拖进茶坊,绳子上磨蹭的痕迹就是拖动时留下的,之后他蜷起沈庭的身体塞在茶柜里,以免有人发现。之所以要延缓两日动手,只是为了制造不在场证明。<br>如果在沈庭失踪的当晚就动手杀人,次日他再去开那扇门,他的嫌疑将会非常大,山民也会作证沈庭失踪那天的傍晚开始他就不在家中,那便麻烦得多了。<br>所以,他缓了两日,那两日他照常在家,并告知邻屋的山民自己次日清晨要去集市,夜半要出门打猎,并询问是否需要给他们带些东西回来。<br>有了人证在,他再下手引来陈肆和赵骞,动手杀人,次日假意路过,就不会有人怀疑。<br>至于为何不把绳子带走,据霍齐说,只是当时慌张,把沈庭从茶柜中弄出来松绑后就忘了带走。<br>简短的“忘了”两个字,让怀疑者无话可说,毕竟他们总不可能拿着自己的猜测去问嫌犯,既然能布置这么缜密的计划,又为什么会忘记带走绳子。<br>月陇西放下筷子,“你觉得他可信吗?”<br>卿如是好笑地点点头,“目前来说,找不出他话中的纰漏。按照他的逻辑捋,似乎没什么好怀疑的。但是,”她话锋一转,“我若信他,就是脑子瓢了。”<br>话音落下,月陇西又从袖中掏出一样用锦帕包裹住的东西,递给她,“你瞧瞧这个。是我从被撞死的地痞脖子上解下来的,原本上面吊着一锭银子,但官差处理尸体时将银子给贪了,为了销赃,昨日便花了出去,现在想找回来怕是不太可能。”<br>锦帕里包裹着的,是一根细绳。<br>她疑惑地打量着这根细绳,脑中被灵光穿透,忽地就想明白了前日一直觉得不对劲的地方。<br>缓缓抬眸看向月陇西,追问道,“那地痞是什么身份?”<br>“乞丐、混混,常年混迹在街边,没有正经活干的人。”月陇西收好那页黄纸,“这个身份,什么都查不了。那日暴雨,又将痕迹彻底冲刷了个干净。最重要的是,这人已经死了,整个扈沽城都知道他死时,脖子上还吊着一锭银子,是个钱串子,为了讹钱才发生的意外。事到如今,沈庭案竟落个查无可查的结果。”<br>他见卿如是陷入了沉思,也没扰她,收好细绳和黄纸,起身离去。<br>这个结果的确出乎意料,卿如是一时懵了,但这不代表她就认可了这个结果。她在凉亭中静坐许久才回到房间。<br>入睡前皎皎来给她上药,与她说起寿宴献礼的事,她长叹一声,盯着自己的小腿怔愣了许久。<br>给郡主作诗一首行不行?敷衍得够明显吗?<br>“姑娘,要不咱就别跟着查那案子了罢?今儿还只是割破皮肉,明儿万一就……”皎皎顿了顿,皱眉道,“现如今姑娘也不练武了,鞭子耍得生疏,若是再碰上个歹徒,不晓得打不打得过。”<br>卿如是点点头,“你倒是提醒了我。”她得把鞭子继续操练起来。在此之前,得先有一根趁手的鞭子。<br>上回使唤麻绳,倒没觉得手有多生,想必要捡起来也快。上辈子她入月府后很长一段时间就没再耍鞭子,谨记她娘的嘱咐,好好当妾,别一天到晚花里胡哨的给月一鸣惹事。<br>哦。<br>可秦卿不拿鞭子给月一鸣惹事,月一鸣就要拿鞭子惹她。<br>有回天气正好,她搬了许多书出来晒,正蹲在院子里翻页呢,月一鸣挽着鞭子凑过来了。<br>他蹲在自己身边,伸手帮她翻了一页书,“秦卿,今早上朝的时候,我被一个半老爷们用眼神猥。亵了。他还言语调戏我,说我生得好看,长眉如墨,眸似星辰,鼻若悬胆,一点朱唇,还真是这样,我都没有理由反驳他。你说气不气人?”<br>“……”秦卿无语,甩下手上的书,朝右边挪了几步,离他远些了才回道,“月狗逼,你都骚到连男人也勾搭了。”<br>月一鸣朝她挪近一步,“回来以后我就在想,男人出门在外得要保护好自己。可惜我是文臣,你说我现在跟着你学学鞭子还来得及吗?”<br>毛病,她自打踹他不成反被拽之后就晓得,这人怎么可能一点武学皮毛都不懂。<br>她随口回,“这鞭子我自小练,不晓得挨了自己多少打才学有小成,你若要练,也得做好被自己打得浑身是伤的准备。”<br>“行啊,没问题。”他站起身,将鞭子递给她,挽着唇角,“请赐教。”<br>话音刚落,秦卿夺下鞭子横空一甩,便耍了一段。<br>那鞭子在她手中破空扬尘,宛若龙蛇,鞭影重重,晃得人眼花缭乱,她翻身腾空,扭腰抡出,凌厉如锋的长鞭势如破竹。<br>待她定睛看时,才发现月一鸣就站在长鞭尽头,可她的手腕已收势不住。<br>那最凌厉的一鞭便抽到了月一鸣的身上,“啪”地一声,险些给他痛出眼泪花来。<br>猝不及防,他倒嘶了一大口凉气,“???”<br>秦卿也吓了一跳,她都忘了面前还有一个人了,“你没事罢?”<br>月一鸣转过背给她看,“你猜我有没有事?”<br>秦卿默然。<br>他又噙着笑,接过她手里的鞭子,玩笑道,“我没事,现在该我了。你站远些,免得我抑制不住自己睚眦必报的脾性。”<br>秦卿赶忙站远了些。他这话说来有些挑衅,秦卿退开时还高看了他几眼,以为他能过目不忘,才看她耍了一遍就能重复个二三四来。<br>后来的事实证明,她果真高看他了。月狗逼在她的注视下,十分壮烈地自残了小半个时辰,共计十三处鞭伤,有重有轻。<br>耍完还一定要问她,“我发挥得还可以吗?”并希望她给出评价和纠正。<br>秦卿:“惨不忍睹。”<br>当晚,月一鸣拿着药来,让她帮忙擦伤处,说是那些下人抹药没轻没重。秉着他开门红的那一鞭出自于她的手,秦卿接过了药。<br>月一鸣脱掉上衣,指了指胸膛,又点了点肩膀后,若有所思,“这鞭痕倒有些均匀,勉强还对称。”研究完伤后,他抬眸挑眉问她,“我伤得还算漂亮吗?”<br>秦卿:“……”<br>她一声不吭地给他上药,拂过胸膛上的鞭痕时,他闷哼了声,“你……”<br>她收手,动作轻了些。<br>他又闷哼,顿了顿,握住她的手重摁在胸口,嘴角勾起笑,“你还是重些罢。好让我清晰地知道是在上药不是在做别的。”<br>秦卿没懂他的玩笑,按照他的要求用了力。<br>他的笑容渐渐消失,脸都白了,“……也不要太重,拿捏个度。”<br>秦卿被他要求来要求去,皱起了眉,不搭理他了。<br>过了一会儿,见她没说话,月一鸣又道,“秦卿,我还有地方没擦。”<br>“什么地方,你直接说罢。”她有些困了。<br>月一鸣:“什么地方你都帮我擦吗?”<br>秦卿:“嗯……”<br>好嘞。<br>“腿根。”月一鸣单手接了腰带,“来罢,我准备好了。”<br>秦卿:“???”扯犊子呢那地方能打到?<br>月一鸣慢条斯理地开始脱亵裤,挑眉道,“打没打到你看了不就知道了。”<br>果然是没打到。不等她发作,月一鸣噙着笑,反剪住她的双手,搂着睡去了,“秦卿,明日也要教我。”<br>次日上朝后,惠帝在书房问他,“爱卿这是……?”<br>月一鸣慵懒地道:“情伤,打情骂俏的伤。”<br>惠帝嫌膈应,特准他在家休假十日。<br>很久之后秦卿才知道,这位口口声声说自己是文臣的人,幼年习武,精通骑射,十五岁那年被月家丢过两回战场,打过胜仗也吃过败仗,当过军师,也跑过小卒,说是月家为了磨砺他的心性。总而言之,不是个蠢到耍鞭子能打得自己遍体鳞伤的。<br>她知道后也问过月狗逼,既然如此,还费那个劲跟她学什么劳什子鞭子。<br>月狗逼拈着没批完的文书笑说,“那半老爷们真对我有意思,我吓得不轻,所以借伤躲了几日。”<br>秦卿不信。<br>他又无奈道,“好罢,跟你说实话,行走江湖,想多学个技艺傍身,以后若是被月家赶出门不当宰相了还可以去街头卖艺。”<br>秦卿不是傻子,当然也不信。<br>他朗声笑,“好罢好罢,就知道你聪明,骗不过你。其实是朝中有人要挑我的事,陛下劝我弄点伤避朝为好。现在风头过了,你看,我这不是在补批欠下的折子吗?”<br>秦卿琢磨了会儿,这才信了。<br>刑部常道,质问三番过后,就该说真话。<br>只不知这真话是真的,还是那人说出来让你以为是真的。<br>本章已完成!
 爱心猫粮1华币
爱心猫粮1华币 南瓜喵10华币
南瓜喵10华币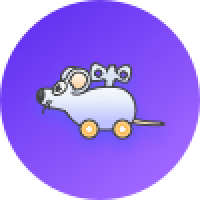 喵喵玩具50华币
喵喵玩具50华币 喵喵毛线88华币
喵喵毛线88华币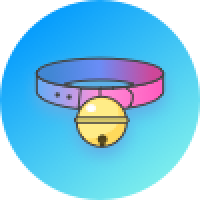 喵喵项圈100华币
喵喵项圈100华币 喵喵手纸200华币
喵喵手纸200华币 喵喵跑车520华币
喵喵跑车520华币 喵喵别墅1314华币
喵喵别墅1314华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