卿如是并不惊讶,她既然知道萧殷就是云谲,那云谲在采沧畔里见过这本书也无甚奇怪。让她疑惑的是,萧殷为何要故意说出这句话。<br>这般说出来,岂不暴露他也在采沧畔有化名且认识叶渠的事实?<br>稍顿,卿如是恍然,抬眸看向萧殷,“你是在根据我的反应试探我?”<br>萧殷:“当我看到那本《史册》的时候就知道,你和叶渠相熟,或许叶渠跟你提过我,而我也刚好在某些方面附和叶渠口中的描述,当我说出方才那句话暴露自己也去过采沧畔,甚至去过叶渠那间书房,你却丝毫不惊讶的时候,我便能确定,你已经知道我的身份了。”<br>他很认真地坦白自己在采沧畔的身份,倒让卿如是有些无所适从。<br>萧殷说完才意识到自己还没有整理衣服,当即又有些脸热,低声道,“我先走了。”<br>卿如是点头,在他转身时,忍不住补了一句,“萧殷,你的文章写得很好。”<br>萧殷礼貌地笑了笑,不再接话。他将文章折好放进袖口中,然后边往外走,边捋衣襟。<br>脸上还留有一抹极其端正的浅笑,却在抬眸看见来人那刻缓缓收敛了。一瞬,眸底涌起些不明的情绪。<br>月陇西的目光落在他整理凌乱衣襟的手指上,逡巡片刻,负在身后的手微蜷握,面上风轻云淡地笑着。<br>萧殷赶忙交叠好衣裳,俯身施礼,“世子,草民是奉几位学士的意思来拿那日写成的文章的。现下拿到了,不敢多作停留。”<br>“不敢多作停留”几个字一语双关。方才拿到文章后就急着走,没有在房间停留。现在得快些走,不能停留。<br>月陇西的视线越过他,看向房间,那里的门还大敞着,卿如是坐在桌前翻书的影子也落在窗上。<br>须臾,他收回视线,“好生作为,收收心,莫要浪费我的推选名额。”<br>“收收心”三个字,亦是一语双关。<br>萧殷低头,“萧殷不敢,必当全力以赴。”<br>月陇西盯紧他的衣襟,“还有,以后来我的院子,须得有我在,若我不在,你就站外边候着。去罢。”<br>萧殷颔首,“是。这就去了。”他垂眸再施礼,待与月陇西错身过后才缓缓直起腰,抬手捋正衣襟。<br>月陇西觉得,屋子那扇门开着,里面还有明亮的灯和捧书的人,就像在等他回家一般。他的好兴致提起来一些,走了两步,回头看了眼刚捋完衣襟放下手的萧殷,收眼时兴致又下了去。<br>尚未走进门,月陇西已抬手将银狐氅脱了。<br>踏进门,解开扣子将外衫脱了。<br>站定于她的房间门口,敲个门等开的工夫,他单手挑了腰带,又脱了一件。<br>待卿如是打开门,赫然就是只着了一身亵。衣的月陇西。<br>上下打量一番,卿如是的目光拂过他身后一地的衣服,最后抬眸看他,皱眉狐疑,“???”这、这么早就睡?<br>“来我房间喝杯茶吗?”月陇西挑眉问。<br>“嗯……好罢。”卿如是紧了紧自己的披风,跟着走过去,待坐定,指着他单薄的亵衣问,“你……不冷吗?今夜风挺大的,我都裹上袄子和披风了。方才萧殷也是,晚上穿得那么少。你们男人是不是身子都要扛冻一些。”<br>“我不冷,我现在很热。”月陇西挽唇淡笑,伸手扒了扒自己的衣襟口,“方才我遇见萧殷时,他正好在整理被扒开的衣襟,想来他也是热着了。”<br>卿如是摇头,如实道,“他跟你不同,我看得出来,都脱成这样了,你是真的热。他好歹穿了三件春衫,扒衣服也不是因为热。”<br>月陇西状似好奇地问,“不是因为热,那是因为什么?”<br>卿如是思考一番,心觉萧殷幼时坐过牢以及心口烙印的事应属私人秘辛,不说为妙,斟酌后便道,“他说他们戏子也是要练身段的,该健壮的地方一点不差。我一时好奇,就让他扒开领口给我摸一下胸。”<br>“……”月陇西:“你摸了?”<br>卿如是理所当然:“摸了。他都脱了我为什么不摸?”<br>月陇西挑眉:“结果呢?”<br>卿如是撑着下颚,“结果,我也没个对比的,不晓得他那算不算健壮。”<br>月陇西沉默半晌,忽然单手扒开衣襟,另一只手丢了张锦帕给她,“来,宽衣,好奇吗你不是?我正好热了,你帮我擦汗,我让你摸个够。然后你再看看他那算不算健壮。”<br>卿如是受宠若惊,“真擦啊?”<br>“你不是看得出来我真热吗?”月陇西松开亵。衣的系带,“背上有些润,瞧不见汗珠子,只得麻烦你挨着挨着擦了。”<br>“行罢。”他都不介意,卿如是也不忸怩,接过锦帕,站到他身后去,抬手帮他扒开衣襟,手还没碰着,她说,“诶我忽然想到一个法子,不必那么麻烦。我去找个蒲扇来,给你扇风不就好了吗?”<br>月陇西:“……”<br>顿了顿,月陇西慢吞吞道:“我忽然觉得又没那么热了。”<br>这句话落得轻,卿如是已将锦帕搭在他肩上,转过背找扇子去了。她房间里的东西齐全,月陇西一早就给她备好了团扇蒲扇一类。<br>她挑了把蒲扇,走过来扒开他的衣裳,挥手扇起来。<br>今夜夜寒,月陇西晚间出门的时候还披了件银狐氅,而今蒲扇起落间,四面八方的风都朝他兜来,那真是钻入骨髓的冷意。<br>究竟是谁欺负谁呢。<br>有幸他体魄好,能让她随意折腾一阵。<br>“你手酸吗?”月陇西的青丝被扇得凌乱不整,在空中飞舞,他有些惆怅,还算淡定地执起茶杯抿了一口茶,气定神闲道,“这么晚了,不如还是早点睡罢。”<br>再扇一会他就要折腾不起了。<br>卿如是声称自己不累。<br>月陇西默然须臾,道,“我累了。”<br>夜凉如水,他究竟在遭些什么罪。<br>不知又过了多久,卿如是终于手酸了,问他,“你还热吗?”<br>月陇西放下茶盏,乖顺回,“不热了。很合适。谢谢你。”<br>走前,月陇西不忘将红绳给她系上。<br>“那好,我去睡了。”卿如是无知无觉,放下蒲扇往自己的房间走,关门前转过头来笑道,“你常年习武,好像是要健壮一些。”<br>语毕,她关上门。<br>月陇西望着那扇门,垂眸低笑了声。<br>勾腰捡了件衣裳起来穿好,月陇西又唤小厮准备沐浴。<br>次日晨起,卿如是闻到一股子药味,她梳洗后出门去看,斟隐正蹲在院子里煎药,看顾着火的那把蒲扇正是她昨夜用的那把。<br>过去一问,斟隐道,“世子说晨起时有些冷,兴许有轻微的风寒之症,害怕真的患上会过病气给旁人,便先吃上一副药预防着。”<br>卿如是蹙了蹙眉,狐疑地思考了下,随即点头,“他人呢?”<br>“月长老找世子有事,一早就出门了。”斟隐说完,揭开药盖,热气扑鼻而来。<br>卿如是抵住鼻子,“这么苦啊?没确定风寒的话就别喝了罢,懒得受这个罪。”<br>“世子吩咐说一定要煎的。”斟隐见她闻着味不舒服,便又将药盖盖上了。<br>卿如是不再扰他,回屋收拾好桌上的文章,准备去找月陇西,将文章交给月世德和卿父。<br>一名小厮带她到月世德的住所,通传后,卿如是等了一会,由小厮领着进屋。<br>她瞧见,月陇西坐在正厅里,不紧不慢地喝着茶,嘴角还噙着若有似无的笑意,看到她来,招手示意她到身旁来坐。<br>待她坐下后,才回答月世德,“长老的护卫又不是陇西扣下的。长老有何不平之处,须得先亲自去刑部报案,立案之后刑部会着手调查,事关重大,我一定让他们认真彻查。待刑部审核清楚之后,若有冤枉了那些护卫的,自然会立即放人。流程给您摆在这里,别的事,陇西也爱莫能助。”<br>月世德的脸色不太好看,有两颗核桃在他手中转来转去,越转越快。<br>卿如是撑着下巴吃糕点,好笑地盯着这僵局。<br>看了一会,视线挪至旁边的长桌,她凝神望去,那桌上似乎叠放的是有待三审的文章。她手里刚好还有一摞,便径直走过去叠在上面,放齐整。<br>两摞待三审的纸堆旁,一摞已经被选定为淘汰的文章,以及一摞选定为通过的文章。<br>卿如是随意浏览了几张,眉头便蹙紧了。<br>后方两人的谈话似乎又到了瓶颈处,暂时揭过话不再说,月陇西朝她走过来,大致也明白她在为何皱眉。<br>卿如是随手翻了翻那堆被选定为不留的,忍了心气,转身问道,“长老的选定策略莫非是但凡崇文党所作便一定不给留?”<br>月世德虚着眼睛看她,“那姑娘的选定策略又是什么?我瞧但凡被姑娘批过的,皆是崇文党所作。说到底,我们都一样。”<br>“修复的是崇文的书,我留下崇文党所作文章有何不对?”卿如是压低声音,“想来陛下让长老进行三审,一定是看中长老德高望重,而不是为了行方便使些龌龊手段。若长老偏要如此大张旗鼓地选些歪瓜裂枣,岂不是在映射陛下其心不纯,下旨修复遗作只是个幌子?”<br>事实就是如此,修复遗作本就是幌子,但月世德手脚做的未免太明显,将崇文党统统排斥在外,这才一选就要把崇文党筛个干净,那后面该如何是好?<br>“卿姑娘牙尖嘴利,老夫说不过你。但你要知道,无论如何,最后遗作修复的成果都会拿给陛下过目。陛下若是不满意,仍会让编修者重头再来,直到陛下达成目的。”月世德起身,走到桌前拿起那一摞被筛掉的文章,递给她,“你尽管拿去重审,留住你想要留的崇文党,结果并不会发生改变。”<br>他如此直白地说出皇帝和他早已预定好的结果,卿如是咬紧牙,竟觉无法反驳。<br>就算选出崇文党来进行修复,最后修补出来的遗作陛下也不会满意,那这一切就都是白费。<br>卿如是凝神紧盯他,情绪翻江倒海。<br>最后,月陇西抬手接过月世德手中的文章,“长老所言极是。她不懂事,想必是不到黄河心不死,那就如长老所言,给她一个机会留下这些崇文党,看看结果究竟会如何。”<br>语毕,月陇西又将那摞文章交给卿如是,缓缓道,“拿着,我倒要看看,留下这些崇文党,结局是否真的会有改变。”<br>卿如是抬眸看他。行罢,给了她一个台阶下。<br>她伸手接过,又抬头去看月世德,极度轻蔑的一眼。<br>收回视线,卿如是转头往门外走。身后,月世德浑浊的眼微微眯起来,“卿姑娘随意翻看便能迅速分辨哪些是出自崇文党之,想来,姑娘对崇文的著作颇有研究。”<br>卿如是并不理会他,抱着文章回到房间。她要在一天之内重审这些被淘汰的崇文党之作。<br>这厢她离去,那厢月陇西还在正厅里吃茶。<br>“陇西,这个姑娘一看就与崇文党的关系密切,你父亲母亲那边就罢了,族里要是知道你看上这么个姑娘,不晓得要怎么说你。你莫要再与她混在一起了。”月世德语重心长。<br>月陇西淡笑,“长老费心。她早与我相看过了,若父亲母亲不同意,也不会安排她与我相看。至于族里,据我所知,月氏如今已不能干涉出仕者的婚配联姻一类。我和她两情相悦,已私自说定终身,过几月我便会去卿府提亲,此事已成定局,长老多说无益。”<br>“两情相悦?说定终身?”月世德嘲,“我怎么就没看出来她对你有别的心思。”<br>“她比较内敛。”月陇西气定神闲,“总之,长老知道她迟早是我月家的人就行了,莫要再找她不自在。刑部那边我会替您打好招呼,尽快将采沧畔的事查清。”<br>月世德敛起嘲意,肃然看向他,“陇西,我的护卫被关进牢里,不会是你在从中作梗罢?我让你动用职权放几个人,你迟迟不肯答应,莫非是在与我虚与委蛇?怎么,我一个月氏长老,还要我来求你不成?陇西,你可莫要……做出背叛月氏的事情来。”<br>本章未完,请翻下一页继续阅读
 爱心猫粮1华币
爱心猫粮1华币 南瓜喵10华币
南瓜喵10华币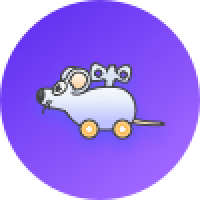 喵喵玩具50华币
喵喵玩具50华币 喵喵毛线88华币
喵喵毛线88华币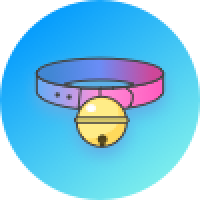 喵喵项圈100华币
喵喵项圈100华币 喵喵手纸200华币
喵喵手纸200华币 喵喵跑车520华币
喵喵跑车520华币 喵喵别墅1314华币
喵喵别墅1314华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