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完,卿如是转身离去,留下皎皎和那名丫鬟站在原地讷然地面面相觑。<br>她不打算回房间跟月陇西共处一室,反倒朝府外走,打算去逛逛书斋,然后回家看看卿母。<br>这厢刚走几步,月陇西就跟了出来,边与她走,边问道,“卿卿要去哪里啊?”<br>卿如是瞥他,“我回家看娘。”<br>“明日就回门了,届时我陪你一道去。”月陇西拉住她,笑道,“你若今日去了,咱娘还以为我欺负你,让你受了委屈。你也不想惹得她担心是不是?”<br>言之有理,卿如是思忖一番,心底妥协,脚却仍是往府外挪,“我去看叶渠。”<br>“看叶渠做什么?他这会正被人围观呢,咱们懒得去凑那个热闹。”月陇西再度拉住她,“待请他入国学府的圣旨下来了,他正式住进国学府后咱们再一起去探望。”<br>饶是心底再次妥协,卿如是仍旧接着往前走,“我去书斋里看书。”<br>“家里不是有很多书吗?”话毕,月陇西瞧着卿如是蹙起的眉,微微一顿,迟疑地问道,“小祖宗是不是哪里不高兴了?谁惹的?”<br>你惹的,就是你惹的。卿如是不予理睬。<br>她觉得月陇西就是个花心枕头,表面上对她千般好万般好,背地里却又和他郡主娘那么远的院子里的小丫鬟勾搭在一起。分明已经在信中对她透露出确认了这位故人的意思,而今两人竟还装作不认识。<br>他左一句“小祖宗”,右一句“怦怦”,其实都是花言巧语。难怪世人常说男人的嘴是骗人的鬼。<br>月陇西瞧她气鼓鼓的模样,一时失笑,“该不会是我惹的罢?为什么啊?”他想起自打昨晚不让她看收藏后她就没说过话,晚上还装睡不肯搭理他,他心底明了了几分。想必是觉得他为人不够坦诚。<br>他只得无奈地笑道,“那好罢,我们去看书。看完书去给你挑胭脂好不好?”他回头望了眼,看见树下那名丫鬟,如果没有记错,今日晨起时应该就是她给卿如是绾发上妆的,他招手唤她过来。<br>“奴婢巧云给世子和夫人请安。”她恭顺地施礼。<br>月陇西吩咐道,“你跟着我们,一会为夫人挑选称心的首饰和胭脂。”<br>巧云应好,卿如是却霎时站住脚,用一种窥破奸。情的目光打量着他们两人,莫名觉得登对之后神情就变得恹恹地,心底烦闷,便往回走,很失落地摇头呢喃,“不去了,我不想去了……”<br>语气近似于看破红尘。<br>月陇西一怔,疑惑地“唔”了声,转身跟着她往回走,犹豫地牵起她的手,却被挣脱了,他再度牵起,与她十指相扣后才问道,“为何不去?”<br>卿如是不答,余光瞧见巧云还跟在后面,她便微微叹了口气,一副老气横秋的样子。<br>“这是怎么了?”月陇西竟被她的样子惹笑了,“是我的错吗?还是小祖宗自己一时想不开了?”<br>卿如是回到房间,坐到书桌后去,自顾自地扒着书看。<br>巧云站在房门口,不知该不该进去,看向月陇西用眼神询问,月陇西使眼色示意她下去。巧云迅速施礼退下。<br>饶是她走得快,但两人这无声的交流落在卿如是的眼中,就成了眉来眼去。她郁闷地支起下颚不去看他们。看书罢,书里什么都有。<br>她翻了两页,发现这本书写得竟然是关于如何喂养莺燕,她默然给合上了。随手又拿了一本,看了一页,发现这竟是一本讲述世家子弟与小丫鬟久别重逢后相知相爱的话本子,她又给合上了。<br>算了罢,书里还真是什么都有。卿如是愁眉不展地捧起两腮,盯着空中一点,忽然想起了月一鸣。还是月一鸣好,好歹他能做到一生一世只喜欢她一个人。有几个男人能做到他那样的。<br>月陇西亦撑着下颚看她,笑吟吟道,“不管是不是我的错,我先给你认个错好不好?您别生气了,气坏了身子……以后不好生孩子。”<br>卿如是瞪他,翻出一摞纸,拿起墨锭要研墨写字,手还没挨着,月陇西抢先道,“我来,我来给你磨。”<br>卿如是没跟他争,当真提蘸墨写起字来,不再理会他。月陇西不知哪里惹着她了,但就这般瞧着她翻书写字也很舒坦,他一手支下颚,一手拿着墨锭在墨池里随意打圈,眼睛都搁在卿如是身上,唇角还挽着笑。<br>如月陇西所料,午时三刻之前,国学府迎来了圣旨。待宣旨的公公回去后,国学府大开府门将叶渠请了进去。圣旨虽开了国学府的门,却也将坊间的舆论和争议推向**。<br>得知这个消息后,卿如是十分担忧叶渠,仍是打算趁早去看望他。毕竟按照月陇西的说法,届时她将崇文遗作修复出来,都是叶老帮她顶罪。叶渠背负着袭檀给他编织的莫须有的骂名这么些年,到时候又要帮她顶个罪名,年纪大了还受这些折腾,她心里实在过意不去。<br>想着,她也不写了,起身收好纸。月陇西微挑眉,“又想去选胭脂了?”<br>卿如是不理睬,唤小厮备马。月陇西一路跟着她,见她似是去国学府的方向,待快要到时便提醒道,“前面有卖墨的,不如给叶老带些好用的去,权当是恭贺他入府了。”<br>卿如是依言拉马去挑选了上等墨,月陇西给了银子,发现她都不等自己的,无奈地笑了笑,挥鞭去追她,与她并辔而行,“小祖宗,你别这样,我都不晓得我哪里做错了,你什么都不说,我现在慌得紧,我怕你回去就休了我。那我岂不是还没尝过女人的滋味就成下堂夫了?恕我直言,这样我以后会没人要的。”<br>她不理,月陇西继续笑着烦她,“哦……我知道了,你不是想休了我,你是琢磨着今晚把我踢下床,不让我睡床了是不是?好好好,我打地铺,我今晚睡地铺还不成吗?榻我都别想睡了,我不配。”<br>她依旧不理,月陇西惨笑道,“还气呀?该不会地铺都不让我打,难道要我就着地毯躺了便是?”<br>“没让你不睡床,你睡你的。”到国学府后卿如是才嗫嚅着回道,勒绳下马,她又有些懊恼自己竟然会允许他继续跟自己睡,于是又改口道,“我去睡榻。”<br>月陇西跟着下马凑过去笑,“那怎么成呢,小祖宗身娇体贵的,着凉了可不得把我给心疼死。啊,说着说着,我这颗赤子之心已经隐隐开始疼起来了呢……”<br>卿如是顿住脚步,忽然转过身,皱眉望他,神情严肃,“我告诉你,你别再嬉皮笑脸的。我不吃这套了!”<br>她这般生气委实有点可爱,月陇西失笑,见她瞪眼,他又立马收敛起笑,故作肃然道,“那好,我现在是端庄稳重的月陇西了。卿姑娘先请——”<br>他说着,抬手礼貌地示意她先走。卿如是咬牙,哼声转头。<br>两人见到叶渠时,脸绷得一个比一个难看。叶渠吹了吹胡须,低头边整理书边问,“怎么了这是?现在最惨的人竟然不是我?”<br>卿如是将要送的墨递去,说明了来意。<br>“没什么可担忧的,放心罢,我活这么大岁数什么风浪没见过了。”叶渠虽然嘴上这么说,神情却有些黯然。他整理书本的动作一直未曾停过,书桌上还摆放着几只陈旧的匣子,他将匣子累到一起,最上面的那只最小。<br>卿如是的目光随着他的手不停移动,最后却被顶面的匣子吸引去,停留在匣盖的花纹上。<br>她微微蹙眉,只觉得这花纹瞧着有些眼熟,像是记忆深处里的东西。<br>叶渠见她盯着看,抬手递给她,“你喜欢就拿去罢。”<br>“啊,不是。晚辈看一看就还给您。”卿如是接过手打量起来,她摸到边角处被灼烧的痕迹,疑惑地问,“叶老,这匣子你是从哪里得来的?”<br>“一直都有,也忘了具体是怎么来的了,只记得是宫里的东西。”叶渠不假思索道,“我用来装些小玩意。用了许多年,我这人念旧,常拿去修补,就是不舍得扔。”<br>“皇宫里的?”卿如是狐疑地蹙眉。她怎么会觉得皇宫里的东西眼熟?倘若是今生的人事物,她合该记得清清楚楚,如今记忆模糊,说明这匣子是她前世在何处见过的,或者说这上面的花纹她前世在哪见过。可前世她从未进过宫,怎么会见过呢?<br>月陇西走过来,低垂着眉眼细看那匣子,同样陷入了沉思,默然不语许久。<br>“既然是宫里的,那多半就是女帝赐给您的,叶老要不您再仔细想一想?”卿如是试探地追问道。<br>月陇西缓缓抬眸,看向叶渠。眸底透露出同一个意思。<br>“你俩真是……”叶渠“哎哟”一声叹,停下了手里的活,坐到椅子上,皱着眉头细细回忆。<br>如卿如是所言,既然是宫中带出来的,那多半是女帝赐的。至于是大女帝还是小女帝,他这也上了年纪了,被赏赐的东西那么多,哪还记得呢?<br>除非赏赐东西时说过什么令人记忆深刻的话,或者发生了什么令人难以忘怀的事。<br>“嘶……”叶渠微眯眼,印象中,这匣子似乎还真佐着那么一段话。<br>“你若被欲。望和权力吞噬,忘掉了初心,那就不该再坐这个位置。你辜负了他的教导。”那男人依旧裹着面纱,跪在她的脚边,嘴里吐出来的,却是冰冷的话。<br>女帝睨着桌上他递上来的匣子,拿起来随意把玩了会,幽幽道,“原本他心目中的既定人选也不是朕。谁都会被权力吞噬,包括原来那个人,那个他亲自选的人。那人只是没有机会接触到这样的权力罢了。这么多年,你不也变了吗?除却样貌,还有心。你的心已不再纯粹,你变得肮脏,你的信仰也已经走向极端,不该再留存于世了。”<br>“话落时,她便将匣子丢下来,甩到了我的脚边。”叶渠皱着眉,“并且十分讥讽地对我说‘这是某人曾经的信念,叶爱卿可要替朕保管好了。’像是专程说与那人听的。”<br>本章已完成!
 爱心猫粮1华币
爱心猫粮1华币 南瓜喵10华币
南瓜喵10华币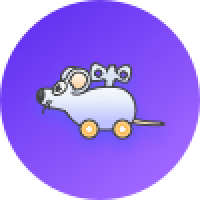 喵喵玩具50华币
喵喵玩具50华币 喵喵毛线88华币
喵喵毛线88华币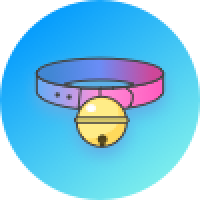 喵喵项圈100华币
喵喵项圈100华币 喵喵手纸200华币
喵喵手纸200华币 喵喵跑车520华币
喵喵跑车520华币 喵喵别墅1314华币
喵喵别墅1314华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