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种感觉,就如同攀登一座险峰时向下俯瞰了一眼,这一眼她看到的是万丈深渊,又无法确定峰下全貌。明明一切都是未知,慌乱却仍在未知的夹缝中生长。<br>卿如是被窗外的光晒得脑袋微微发烫,肉眼可见,顺着窗花透来的缕缕光丝中有浮尘万千,它们轻细而渺小,在热风中升腾。她来晟朝几月,而今终于有强烈的隔世之感。<br>她好像看清了自己原来的那个世界是如何在岁月中慢慢被湮灭,逐渐被黑夜吞噬的,而如今乾坤颠倒,阴阳构建出的另一个世界,黑白是非似乎已有别的标准和界限。<br>“崇文先生,今日雨后现长虹,我看了许久,有一惑至今未解。世间之色如长虹般绚烂多姿便已足矣,为何还要有黑白?”<br>“唯有黑白纯粹至极,你再也找不出两种色彩如黑白一般泾渭分明,却又包罗万象。这大概也是上天赠予世间最美好的祝愿,他愿这世间的人事物生来纯粹,非黑即白。可是我告诉过你的,事物姑且不谈,从来没有人是非黑即白。你喜好诗酒风。流,也可能杀人如麻;你喜好山水字画,或许也嗜血成性。既然俗世不分善恶,那么人便总是时而善,时而恶。”<br>他一顿,轻道,“但那些舔刀饮血,过尽千帆之后,仍存有赤子之心的人,要更美好一些就是了。”<br>“会有那样的人吗?”<br>“有的,秦卿。”他盯着她,别有深意地说,“有天清晨,我看见一个在战场上杀人不眨眼的魔头铩羽而归,他的手沾满鲜血,背上的族旗被杀戮洗涤,佩剑之下亡魂无数。一定意义上来讲,他是个十恶不赦的人,但他悠然打马过长街,摘下一朵洁白的栀子,弯腰送给了一位小女孩。一双沾满鲜血拿刀屠戮的手,却拈住了一朵洁白的花……那一刻,我觉得身旁清风都化为了绕指柔,继而,我愈发笃定我一直深信不疑的一个道理——”<br>“人的复杂恰是生而为人最为精彩之处,黑白分明的从来都不是人,把黑白搅和在一起,灰色的那个,才叫做人。也正因为灰色混沌且浑噩,寻常看来不足为奇,当着重彰显出纯白的那刻,才会予人以惊艳。反之,就会教人难以接受。”<br>如今再回首这段话,卿如是终于悟出它并非仅作教导之说,或许那时候崇文先生话外便有所指。<br>她不敢细想下去,也无法相信自己方才那短短一瞬间迸发的一切荒谬念头,更不愿意让这些念头在思绪中发散。她及时打住,不再去想。惟愿思绪停留在前一刻,方才灵光一闪间想到的都是臆测。<br>月陇西牵住她的手,轻道,“你的呼吸很乱。”<br>卿如是回过神,神情滞涩而迷惘,她望着月陇西,忽然很害怕。颠倒梦幻,不知真假,她害怕眼前的一切都是假的,只是在做一个隔世的梦,为了教她认清一些事,等醒过来之后,她仍在前世。<br>“我忽然想起曾经看过的一本书,一时困惑,难以自拔。”卿如是轻诉,“我不明白,何为真实。倘若我如今的认知将从前一个个认知都推翻了,那我从前经历过的那些就不是真实的了吗?那从前面对虚假的我还是不是真实的呢?或者,从前的是真的,现在认知与从前不同的我才是假的?……”<br>她喃喃自语,似陷入魔障。月陇西轻笑了声,“你们搞思想的都这么玄吗?你想知道你自己是不是真实的,根本不必用辩证的思想让自己陷来陷去。你运气好,这个问题我以前也恰好想过,你知道我是如何想通的吗?其实是个很简单的逻辑。”<br>“怎么想通?”卿如是迷茫地看他。<br>月陇西见她的注意力被吸引,不再放到崇文的事上面,心底轻舒了口气,进而笑道,“这就要说回到方才你向我提出的刁难上面了。”<br>“刁难?”卿如是想了想,撇嘴道,“你说那两片一模一样的叶子?”<br>“嗯。”月陇西笑着颔首,稍一挑眉,“叶子我马上就能拿出来给你看,你等着我。”<br>卿如是疑惑地看着他转身去的方向,须臾,不知他拿了什么回来握在手里,不待人看清,他便拉着她的手往门外走。<br>“去哪儿啊?”卿如是皱眉,“不是要看一模一样的叶子吗?”<br>月陇西笑吟吟道,“是啊,我给小祖宗寻个没人的地方,以免你输了不好意思亲。”<br>卿如是虚起眸子打量他,心底的好奇更甚。<br>两人来到一片幽静的树林,月陇西将她抵在一棵树下,慢悠悠地抬手,赫然是一杆细长的,正飞快地在他掌心和指尖打着转。<br>“什么啊?”卿如是狐疑地盯着他。<br>他勾唇,不疾不徐地用左手在自己右手掌心画了一片叶子,在她似有明了的眼神中,一边真挚地凝视着她,一边牵起她的手,与自己十指相扣,紧紧一握,将人给拽进了怀里。<br>卿如是低呼了声,另一只手下意识伏住他的肩,抬眸羞怯地瞪他。<br>“唔……”月陇西松了右手,摊开掌心,与她的手掌并排在一处,示意她看,“如何?”<br>只见他们两人掌心各有一片叶子,形状大小颜色皆无异,甚至因为墨汁色深,刚画的脉络都印得清清楚楚,无半点分别。<br>卿如是蹙眉羞恼,“你、你这分明是耍赖啊!”<br>“嗯?我看你这态度,你才是想耍赖的那个罢?”月陇西挑眉,笑道,“你只说是叶子,也没说不能是这样式的啊。你可别又跟我赖?我们可是击掌为誓了的。”<br>卿如是面色烫红,低头嗫嚅道,“可是……你自己也说,这世上本就没有一模一样的两片叶子,我不就是冲着这点才跟你击掌为誓的吗?我承认我故意刁难你,可你也是一早就想用这般刁钻的法子来应付我,我们谁也别说谁……”<br>月陇西轻抬起她的下颌,玩味地笑,“你瞧瞧你这说的是人话么?既然我已经明确告诉你这世上没有两片相同的叶子,那你还跟我击掌,你是不是太恶毒了些?我不管,你答应我了。”<br>“哎呀可是我……”卿如是低头,面红耳赤地跟他讲道理,“我以为我稳赢的,压根就没做好这方面的准备……”<br>“一回生二回熟,你闭上眼睛亲一回,下回就不需要劳什子准备了。”月陇西单挑左眉,“再说,只是让你主动而已,咱们又不是头回了。”<br>卿如是咬唇,手臂还耷在他的颈边,片刻后转过头憋出几个字,“我不好意思,没有经验……我、我可不可以赖掉啊?”<br>饶是对结果本就不抱有太大期望,月陇西仍是哀叹了一声,失落地垂下眼睫,怅然站在树下良久,又忽然无奈地笑起来,揽着她的腰轻道,“你啊你,真是疼死我了,要我的命……”<br>他的话尚未说完,卿如是倏地踮起脚尖,轻跳起身,在他的侧颊上亲了一口。<br>浅浅的一声,清脆好听。一瞬如冰雪消融,春暖花开。<br>方才忽地迎面袭来的淡淡清香还萦绕在鼻尖,侧颊被她吻过的地方微微酥痒发烫,月陇西讷然回味着,慢吞吞地低头看向她,“?”<br>卿如是故作自在地瞟向别处,嗫嚅道,“脸上……可以。”<br>月陇西唇角缓缓翘起,直勾勾地盯着她,手指端起她的下颌,摩挲着她的唇瓣,俯身就要亲,“那这里我来代劳……”<br>尚未触碰到,猛地被卿如是推开,她不满地蹙眉,用很认真的语气教育他道,“你今天亲太多次了,不能再亲了,节制一点。”<br>“???”月陇西眉心微皱,苦口婆心地道,“小祖宗,求求你了,节制不是用在这方面的,我想亲你一口每天还有限制?您就别折腾我了。”<br>卿如是拧着不给亲,“但是我今天还帮了你的忙,你最少应该有一个月都不会再有这方面的想法了罢?一月之内,你不能再提让我帮忙的要求,顺便也就不能再亲我。”<br>她深深记得,上辈子自己很不明白男人怎么会那么喜欢做这种羞耻的事,于是提议月一鸣如果有需要,那么就一年来找她一回,她可以帮他。月一鸣听后险些吐血,随即义正言辞地告诉她,男人几乎都是一个月需要一次纾解,一年一回是不现实的。<br>虽然月一鸣那厮并没有做到一月一次,往往坚持不到十天就破了功。但一个月一回这个规律卿如是一直记到现在,料想月陇西也该是这么个规律。<br>月陇西:你料想个鬼。<br>他听到“一个月”三字时就很清楚地知道卿如是想到了什么,然则,前世是她先提出“一年”的限制,他当然不敢往太短的时间说,免得彼时对他根本没有好脸色的秦卿会直接拒绝,于是他才十分客气地搬出“一月”来哄她。<br>如今两人的关系突飞猛进,前世根本无法相提并论。他觉得自己天天跟她来几回都有可能,让他等一月一回,还不准亲……真是信了她的邪。<br>“你怎么会有这种奇怪的想法?”月陇西故作从容地循循善诱,“正常的男人每天都有可能陷入欲。望的挣扎之中。稍微严重些的可能一天挣扎好几次。你要我一个正常男人活生生憋整整一个月,不觉得你自己有点叛逆有点残忍吗?”<br>“你别耍嘴皮子,就这么定了。再说,再说就再也不帮你了。”卿如是微睁杏眸,正色道,“你方才要跟我解释的问题呢?我要听那个,不要听你说这些乌七八糟的东西。”<br>月陇西看向别处,怅惘地叹了口气,未言。<br>卿如是正儿八经地问他,“你叹什么气?”<br>月陇西亦正儿八经地回她,“我脑袋疼,叹口气缓解一下。”<br>“快点,我要听答案。什么是真实?你画也画了,我亲也亲了,你却还未告诉我。”卿如是果不其然还是那个一心向道的卿如是,皱着眉以一种渴学的态度询问道。<br>月陇西无可奈何地睨她一眼,再度悠悠叹了口气,盯着她盯了好一会才翘起唇角,认栽了。<br>“很简单。”他抬手帮她拂过飘到眼前的青丝,摊开掌心,柔声说道,“这叶子虽是画的,但我拿它来哄你,不仅哄住了你,你还愿意兑现承诺亲我,是因为这片叶子本身是真实的吗?当然不是。那是因为你愿意相信它是真的,既然愿意相信,便姑且当它就是真实的罢。”<br>“这世间走一趟,真假从来难说,眼见的耳听的都很难被称为真实,因为所有如今既定的事实都太容易被以后推翻,唯有自己相信的,才永远不会被推翻。今朝你可以相信这个说法,明朝你也可以相信的说法,你所相信的事物一直在变,如此,你便一直是真实的,做不得假。”<br>本章已完成!
 爱心猫粮1华币
爱心猫粮1华币 南瓜喵10华币
南瓜喵10华币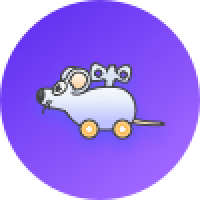 喵喵玩具50华币
喵喵玩具50华币 喵喵毛线88华币
喵喵毛线88华币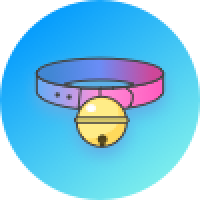 喵喵项圈100华币
喵喵项圈100华币 喵喵手纸200华币
喵喵手纸200华币 喵喵跑车520华币
喵喵跑车520华币 喵喵别墅1314华币
喵喵别墅1314华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