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辞旧迎。)<br>竹楼这边的动静实在太大,裴钱给惊醒后,立即穿好衣裳,配好刀剑错,手持行山杖,冲出门去。<br>粉裙女童晚于她半步,也打开了屋门,见着了裴钱快步奔出院子的灵巧背影,粉裙女童便瞅出些异样,赶紧掠去,跟裴钱,果然看到裴钱板着脸,杀气腾腾,一边跑一边嘀嘀咕咕,粉裙女童大致清楚裴钱的脾气,赶紧劝说道:“可别冲动啊,老爷早些年在山练拳,一直是这样的。”<br>粉裙女童倒不是不心疼自家老爷,而是知晓轻重利害,不愿意裴钱在竹楼那边吃亏,何况崔老先生,对老爷真没坏心。<br>裴钱握埋头狂奔,紧行山杖,气呼呼道:“老王八蛋真是要造反,这座山头都是我师父的,竹楼更是我师父的,老家伙死皮赖脸霸占着二楼不说,师父才刚刚山,被两三拳打晕过去,一睁眼,不过是与我们聊了会儿,没过多久,又挨了拳头,现在又来!师父是回家乡享福的,不是给老家伙欺负的!”<br>裴钱越说越恼火,不断重复道:“气煞我也,气煞我也……”<br>粉裙女童到底是一条跻身了五境的火蟒精魅,轻灵飘荡在裴钱身边,怯生生道:“崔老先生真要造反,我们也没辙啊,咱们打不过的。”<br>裴钱歪头吐了口唾沫,没有放缓脚步,咬牙切齿道:“那不打架,我跟老王八蛋讲理去!我不信邪了,天底下还有这样不厚道的客人,欺负我师父好说话不是?我裴钱可不是什么善茬!我是师父的开山大弟子,是崔东山的大师姐!”<br>粉裙女童倒退着飘荡在裴钱身边,瞥了眼裴钱手的行山杖,腰间的竹刀竹剑,欲言又止。<br>裴钱住处附近,青衣小童坐在屋脊,打着哈欠,这点小打小闹,不算什么,起当年他一趟趟背着浑身浴血的陈平安下楼,如今竹楼二楼那种“切磋”,像从边塞诗翻篇到了婉约词,不值一提。裴钱这黑炭,还是江湖阅历浅啊。<br>郑大风在和朱敛在院饮酒赏月,不聊陈平安,只聊女人,不然两个大老爷们,大晚聊一个男人,太不像话。<br>朱敛聊那远游桐叶洲的隋右边,聊了太平山女冠黄庭,大泉王朝还有一个名叫姚近之的狐媚女子,聊桂夫人身边的侍女金粟,聊那个脾气不太好的范峻茂。<br>郑大风便聊了已经叛出神诰宗的贺小凉,不幸跌入山下泥泞的正阳山仙子苏稼,大骊那位身材矮小却风情万种的宫娘娘,后来扯远了,郑大风还聊到了早年给骊珠洞天看大门那会儿,在小镇土生土长的出彩女子,有泥瓶巷顾氏,更早几十年,还有杏花巷一位妇人,前些年才当了龙须河的河婆,成为山水神祇后,得以返老还童,恢复了年轻时候的姿容,长得真是不赖,可是嘴巴刻薄了点,吵起架来,他嫂子还要厉害几分。<br>郑大风抿了口酒,砸吧砸吧嘴,满脸陶醉,“月夜清风,与挚友畅饮,说尤物美妇,真是神仙日子。”<br>桌这套青瓷酒具,有些年月了,一看是小镇一座龙窑烧造出产,几近完美,作为大骊宋氏的御用贡品,按照惯例,稍有瑕疵的次品,一律会被窑务督造官衙署的官吏,严格筛选出来,敲碎后丢在老瓷山,郑大风爱喝酒,脑子又灵光,偷偷弄来些本该搁置在大骊皇宫的瓷器,不难。对于郑大风这些狗屁倒灶的小事,药铺杨老头当年估计都不稀罕搭一下眼皮子。<br>朱敛正提起酒壶,往空荡荡的酒杯里倒酒,突然停下动作,放下酒壶,却拿起酒杯,放在耳边,歪着脑袋,竖耳聆听,眯起眼,轻声道:“富贵门户,偶闻瓷器开片之声,不输市井巷弄的杏花叫卖声。”<br>朱敛听过了那一声细微声响,双指捻住酒杯,笑语呢喃道:“小器大开片,仿佛乡野少女,情窦初开,兰花香草。大器小开片,宛如倾国美人,策马扬鞭。”<br>郑大风听着了这些颇为醋酸的人措辞,竟是半点不觉得别扭,反而跟着朱敛一起怡然自得。<br>照理说,一个老厨子,一个看门的,只该聊那些屎尿屁和鸡毛蒜皮才对。<br>明月朗朗,清风习习。<br>对坐两人,心有灵犀。<br>人间美事,不过如此。<br>郑大风笑道:“朱敛,你与我说老实话,在藕花福地混江湖那些年,有没有真心喜欢过哪位女子?”<br>朱敛轻轻放下酒杯,感慨道:“喜欢女子之时,岂可不真心,岂敢不用心。只是家国江湖,处处事事,身不由己,年轻的时候,心天高,总觉得男女情爱,风流极致犹嫌小。纵横捭阖,功高盖世,力挽狂澜,青史留名,早年在书一瞧见这些个词,像……”<br>郑大风顺嘴接话道:“跟一条老光棍在深山老林,窥见了美人出浴图,一下子热血头了。”<br>朱敛赶紧给双方倒满酒,凭这句话,该满饮一杯。<br>两人轻轻磕碰,朱敛一饮而尽,抹嘴笑道:“与挚友酒杯磕碰声,那豪阀女子沐浴脱衣声,还要动人了。”<br>郑大风问道:“如此天籁,你真听过?”<br>朱敛点点头,“过眼云烟,俱往矣。”<br>郑大风心悦诚服,竖起大拇指,“高人!”<br>青衣小童翻了个白眼,实在想不明白,这两个武夫,怎么只要厮混在一起,既不聊武学,也不大碗吃肉,偏偏聊那吃也不能吃、还最耗钱财的女子,女子长得再好看,又能如何?凡俗夫子,即便如花似玉,花能开多久?人老珠黄又需要几年?便是山女修,再好看,可好看能当饭吃吗?能当神仙钱买法宝吗?青衣小童觉得这两人的江湖,真俗气,太无。<br>关键是郑大风也好,朱敛也罢,分明都是宝瓶洲最出类拔萃的纯粹武夫,既然如此爱慕女子颜色,又偏偏身边一个佳人也无。<br>世俗江湖,所谓的江湖宗师,哪怕不过六境七境,想要偎红倚翠的话,还不简单?<br>青衣小童后仰倒去,双手作枕头。<br>他想不明白,为什么陈平安能跟他们做朋友。<br>而且是真正的朋友。<br>竹楼那边,裴钱见着了站在二楼廊道的光脚老人。<br>老人笑问道:“怎么,要给你师父打抱不平?”<br>裴钱眨了眨眼睛,“老先生,咱们都是混江湖的英雄好汉,所以要讲道义,要知恩图报,对吧?”<br>老人没有说话。<br>他俯瞰着那个怎么看怎么都是块武运胚子的黑炭丫头,有些纳闷,屋内那小子怎么舍得不用心雕琢这块绝世璞玉,陈平安这家伙别的不说,眼光还是有点的,不该瞧不出裴钱的天资根骨才对。怎的由着楼底下这个小惫懒货吃不住疼,真不去刻苦习武了,成天想着一夜练出绝世剑术,两天练出个天下无敌。<br>只是小丫头认了陈平安当师父,还算死心塌地,那么老人不好随便插手,这才是真正的江湖道义。哪怕小黑炭每天游手好闲,暴殄天物,老人也只能等到陈平安返回落魄山,才好说道一二,至于最后陈平安如何对裴钱传授武学,依旧是这对师徒二人的自家事。<br>老人不说话。<br>裴钱越没有底气,打是肯定打不过的,喊老厨子都么得用,还是怪自己那套疯魔剑法太难练成,否则哪里容得老王八蛋如此嚣张跋扈,早打得他跪地磕头,给自己师父认错了。<br>只是裴钱今儿胆子特别大,是不愿转头走人。<br>粉裙女童扯了扯裴钱的袖子,示意她们见好收。<br>裴钱轻轻拍掉粉裙女童的手,昂首挺胸,大声道:“老先生,咱们下五子棋,规矩由我来定,谁赢了听谁的,敢不敢?!”<br>老人面无表情道:“不敢。”<br>裴钱愣在当场。<br>老人突然说道:“是不是哪天你师父给人打死了,你才会用心练武?然后练了几天,又觉得吃不消,干脆算了,只能每年像是去给你师父爹娘的坟头那样,跑得殷勤一些,可以心安理得了?”<br>裴钱眼泪盈盈,紧抿起嘴,伸手死死握住腰间刀柄。<br>在此时,一袭青衫摇摇晃晃走出屋子,斜靠着栏杆,对裴钱挥挥手道:“回去睡觉,别听他的,师父死不了。”<br>裴钱泫然欲泣道:“万一呢?”<br>陈平安气笑道:“那楼,师父让他帮你揉拿筋骨,跟隋右边当时在老龙城差不多,要不要?我数到三,如果还不回去睡觉,把你抓来,想跑都跑不了,以后师父也不管你了,一切交由老前辈处置。”<br>陈平安刚数了个三。<br>裴钱开溜了,一边跑一边嚷嚷道:“没有万一,哪有什么万一,师父厉害着哩。”<br>老人冷笑道:“良心也没几两。”<br>陈平安咳嗽几声,眼神温柔,望着两个小丫头片子的远去背影,笑道:“这么大孩子,已经很好了,再奢望更多,是我们不对。”<br>老人摇头道:“换成寻常弟子,晚一些晚一些,裴钱不一样,这么好的苗子,越早吃苦,苦头越大,出息越大。十三四岁,不小了。如果我没有记错,你这么大的时候,也差不多拿到那本撼山拳,开始练拳了。”<br>陈平安笑道:“反正我才是裴钱师父,你说了不算。”<br>老人斜眼道:“怎么,真将裴钱当女儿养了?你可要想清楚,落魄山是需要一个无法无天的富家千金,还是一个筋骨坚韧的武运胚子。”<br>陈平安双手放在栏杆,“我不想这些,我只想裴钱在这个岁数,既然已经做了许多自己不喜欢的事情,抄书啊,走桩啊,练刀练剑啊,已经够忙的了,又不是真的每天在那儿游手好闲,那么总得做些她喜欢做的事情。”<br>老人问道:“小丫头的那双眼睛,到底是怎么回事?”<br>陈平安摇头道:“从藕花福地出来后,是这样了,东海观道观的老观主,好像在她眼睛里动了手脚,不过应该是好事。”<br>老人不是拖泥带水的人,问过了这一茬,不管答案满不满意,立即换了一茬询问,“这次去往披云山,谈心过后,是不是又手欠了,给魏檗送了什么礼物?”<br>陈平安有些尴尬,没有隐瞒,轻声道:“一块杜懋飞升失败后坠落人间的琉璃金身碎块。”<br>老人是见过世面的,直接问道:“多大。”<br>陈平安回答道:“孩子的拳头大小。”<br>陈平安本以为老人要骂他败家,不曾想老人点点头,说道:“不能只欠魏檗的人情,不然将来落魄山众人,在心境,被你连累,一辈子寄人篱下,抬不起头来看那披云山。”<br>老人又问,“知不知道我为何两拳将你打到溪畔的阮秀身前?”<br>陈平安摇头。<br>老人说道:“阮秀当年跟随粘杆郎去往书简湖,知道吧?”<br>陈平安点头道:“差点碰面。”<br>老人嗤笑道:“那你知不知道她宰了一个大骊势在必得的少年?连阮秀自己都不太清楚,那个少年,是藩王宋长镜相的弟子人选。当初在芙蓉山,大局已定,拐走少年的金丹地仙已经身死,芙蓉山祖师堂被拆,野修都已毙命,而大骊粘杆郎却完好无损,你想一想,为何没有带回那个本该前途似锦的大骊北地少年?”<br>陈平安是真不知道这一内幕,陷入沉思。<br>老人泄露了一些天机,“宋长镜相的少年,自然是百年难遇的武学天才,大骊粘杆郎之所以找到此人,在于此人早年破境之时,那还是武道的下三境,引来数座武庙异象,而大骊向来以武立国,武运起伏一事,无疑是重之重。虽说最后阮秀帮助粘杆郎找了三位粘杆郎候补,可其实在宋长镜那边,多多少少是被记了一账的。”<br>陈平安疑惑道:“跟我有关?”<br>老人差点又是一拳递去,想要将这个家伙直接打得开窍。<br>陈平安心有所动,已经横移出去数步,竟是逆行那撼山拳的六步走桩,并且无自然。<br>老人稍稍消气,这才没有继续出手,说道:“你只争最强二字,不争那武运,可是阮秀会这样想吗?天底下的傻闺女,不都是希望亲近的身边男子,尽可能得到万般好处。在阮秀看来,既然有了同龄人,蹦出来跟你争抢武运,那是大道之争,她是怎么做的,打死算数,斩草除根,永绝后患。”<br>陈平安神色黯然。<br>老人一手负后,一手摩挲栏杆,“我不乱点鸳鸯谱,只是作为了岁数的过来人,希望你明白一件事,拒绝一位姑娘,你总得知道她到底<br>本章未完,请翻下一页继续阅读
 爱心猫粮1华币
爱心猫粮1华币 南瓜喵10华币
南瓜喵10华币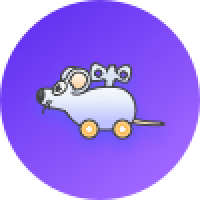 喵喵玩具50华币
喵喵玩具50华币 喵喵毛线88华币
喵喵毛线88华币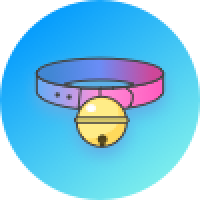 喵喵项圈100华币
喵喵项圈100华币 喵喵手纸200华币
喵喵手纸200华币 喵喵跑车520华币
喵喵跑车520华币 喵喵别墅1314华币
喵喵别墅1314华币

